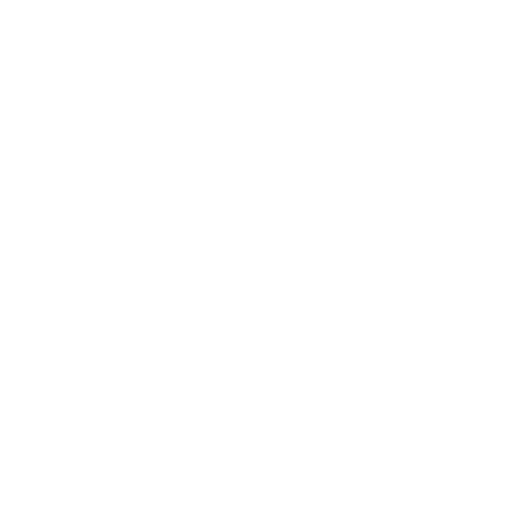“带1000万全球青少年儿童了解浙江”,当高总和老魏说出这个目标时,语气里没有丝毫张扬。
这个看似宏大的愿景,藏着他从出境游车导到文博研学创业者的十年辗转文旅路。
前段时间,我采访了一位在杭州做研学旅行的创始人高总,我还是先说结果,他2021年开始做青少年文博研学产品的研发,2024年一个暑期就接待了超过500个研学团,收入数百万。
他是如何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在这么卷的市场里,做出自己的特色和相对优势的呢?
今天老魏给大家讲讲高总的文旅创业故事和转型升级路径。
从境外向导到杭州文旅创业者的波折历程
2013年左右,还在美国留学的高总,在课余时间做起了“司机兼导游”的工作。
他清晰的记得第一次接到的订单,是来自上海的一家三口游客的加州之旅,当他带着家长和孩子看博物馆时,总是问些很深的问题,逼得他连夜查资料。
那段经历让他发现,旅行者对“有内容的体验” 需求强烈。
2015年回国后,他加入之前入驻过的那家出境向导服务互联网平台团队担任产品总监,负责研学线路开发。
但随着阿里注资后,那家的公司战略调整,他逐渐意识到跨境向导服务的局限:“利润太薄,10%的抽成根本覆盖不了人力成本”。
2018年,他组建团队,尝试做定制游,却很快陷入困境,主要原因是他当时觉得定制服务太耗人,自己无法承担组建更大的服务和技术团队的成本。
转折出现在2019年。当时他们转向垂直领域,带全国花艺师赴欧洲考察,业务刚有起色,2020突如其来。
所有出境业务停摆,团队8个人盯着电脑发呆,高总苦笑称那段时间是 “被迫转型”。
不能出国的日子里,他把目光投向国内。
他自己出行就喜欢学点东西,不然觉得浪费时间。当时就想,能不能做知识型的体验?
最初他们带成人探访麦积山、三星堆,但三年的反复让长途出行受限,加上成人消费力下降,业务难以为继。
2021年夏天,在浙江博物馆的一次考察中,他发现了新的可能,国外博物馆教育很成熟,国内却很少有人专门做,北京,上海有人刚起步,杭州还是空白。
就这样,他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青少年文博研学领域。
从0到1的研学课程该如何做?
刚开始在博物馆上课,连个固定场地都没有,高总回忆创业初期的窘迫。
他们曾在博物馆的走廊里给孩子讲青瓷,在遗址公园的树荫下开展陶艺体验。
最棘手的是课程设计,当时行业里都是一个馆一个课,同质化严重。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省博物馆他做了4套课,有专门讲陶瓷的,有聚焦宋代文化的,甚至能拆解出‘十大镇馆之宝’专项课程。
这套“拆解法” 背后是严苛的研发流程。团队7个人,有历史系硕士,有小学教育背景的老师,还有前媒体人,他们像 “编辑部” 一样工作,查史料、写脚本、磨课件。
一套课的基础资料就要3-4万字,加上延伸阅读能到10万字,高总翻出电脑里的课程库,你看这个良渚玉器课,光参考文献就列了27篇,包括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
为了让孩子听得懂,他们发明了“学术翻译” 机制。专家讲的术语要转化成孩子能理解的语言,比如把‘失蜡法’说成‘古代的3D打印’”。
所有课程都要经过 “三审三校”,历史学者审准确性,教育专家审适龄性,一线老师试讲课效。
2021年推出的 “南宋美学” 课程,仅打磨就用了6个月,光试听课就开了12场。
师资团队的建设同样不易。他们试过请大学教授来讲,结果孩子坐不住,找导游又太江湖气,讲不深。
最终他们确立“全员讲师” 制度,内部培养+兼职筛选。全职7人必须能上课,80多名兼职老师要通过严格培训,不仅要背逐字稿,还要会控场,能应对孩子的突发提问。
有位历史系毕业的兼职老师,为了讲好“河姆渡文化”,连续一周泡在博物馆,跟着研究员学习器物修复。
研学产品的销售模式,To C还是To B?
高总团队如何获客呢?他们不是直接招生的机构,更像“研学供应商”。杭州市新华书店、大型教育集团都是他们的客户,这些机构采购课程后再卖给C端家长。
这种To B模式的优势在疫情期间显现,高总说,这些机构抗风险能力强,只要他们有需求,他就能活下去。
2024年暑假是个转折点。当时杭州多家旅行社接到外地研学团,急需博物馆课程支持,他们承接了500场课,老师从早上9点讲到下午5点,一天2场,连轴转。
最忙的时候,有位老师在浙江省博物馆连续驻场45天,每天讲‘十大镇馆之宝’,嗓子哑了就含着润喉糖上。
他通过 “碎片化服务” 的定价模式,高总算过一笔账:去除老师课时费和物料成本,公司毛利率能稳定在60%。量越大成本越低,所以他们拼命跑量,去年光暑假就做了500场大课。
但To B模式也有短板,市场声量小,很多同行不知道他们。他们的获客主要靠转介绍。
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开始参加行业比赛,2023年拿了浙江省研学课程大赛金奖,获奖后明显感觉咨询多了,有博物馆主动来找他们合作开发课程。
产品运营如何穿越产业周期?
小团队如何仍做到精细化运营呢?高总主要靠四招:
第一,“文旅这个行业淡旺季太明显,暑假忙到飞起,冬天闲得发慌”,高总摸索出一套弹性运营机制。
旺季时,兼职老师能扩充到100人,全职团队全员上阵;淡季就调休,去年12月,他们轮着放了20天假,趁机打磨新课程。
第二,人力成本控制是关键。养太多人不现实,他们7个全职负责研发和对接,兼职老师按场次结算。
第三,课程标准化是另一大法宝。所有老师都要按“脚本” 上课,不是死记硬背,而是确保核心知识点不跑偏。
他们开发了一套培训体系,新老师要通过“三阶考核”:先背课,再试讲,最后带真实团。
有个老师讲‘越窑青瓷’,试了5次才通过,就是因为没能把‘秘色瓷’讲得让孩子感兴趣。
第四,与博物馆的关系维护则需要“细水长流”。刚开始去对接,人家觉得他们是小公司,不太搭理。
他们就从免费服务做起:帮博物馆整理青少年教育资料,在志愿者活动中承担讲解。慢慢建立信任后,博物馆开始开放资源。
如何围绕研学业务做多业态布局?
光靠研学课程是不够的,他把公司定位为一家文化公司,不是单纯的旅行社,高总有着更长远的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2023年,他们启动了图书出版项目,第一本关于大运河题材的图书已进入校样阶段,这本书脱胎于他们的大运河课程,把讲给孩子的内容系统化了。
文创开发也提上日程。他们做‘瓷器修复’体验时,很多家长想要同款工具包,于是他们联合非遗传承人开发了研学教具套装。
接下来还计划把课程转化成音频课,和教育平台合作,扩大覆盖面。
对外合作方面,他们采取“投资 + 赋能” 模式。南京有个团队做了多年,但模式不清晰,他们投了一部分资金,帮他们建课程体系,现在他们和南京博物院合作上了。
太原、西安的合作也类似,不控股,主要输出经验,当地团队更懂资源。这种模式既控制风险,又能快速复制,去年南京公司的营收已经超过他们在杭州的一半了。
政府资源的对接是意外之喜。因为课程做得扎实,当地产业引导基金在他们创业第二年就投了一笔天使资金,虽然不是很多,但算是有了政府国资背书。
现在他们还承接了浙江省文旅部门的部分项目,帮乡村博物馆做课程设计,他在一步一步的践行‘带1000万孩子了解浙江’的初心”。
行业大洗牌中该如何坚守?
这两年研学市场很乱,家长“游而不学”、“研而不游”、“价格混乱”的吐槽越来越多,高总对行业现状有着清醒认知。
他见过太多机构赚快钱,收20次课的钱,只上5次就跑路,这也是他们坚持To B、不做C端储值的原因,每笔预存款都是债务,没交付他就不踏实。
在他看来,研学旅行市场正在分化。科技类研学看起来更值钱,家长更愿意买单。
他们做的人文类研学,价值感没那么直观。但他坚信长期价值,孩子们看博物馆虽然不是刚需,但审美和历史认知是会受益一辈子的事。
为了提升竞争力,他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互动元素,在产品研发上更加较真儿了,这种“较真儿”的态度,让他们在行业大洗牌中站稳了脚跟,今年市场不好,很多机构收缩,他们反而接了更多同行的外包。
对于未来,高总很坦然,不再追求上市那种宏大叙事了,想慢慢做,先把杭州的模式跑透,陆续再辐射浙江,然后布局全国。
毕竟仅浙江全省就有大大小小300多家博物馆,他们才做了30多个,路还很长。
高总最后意味深长的对老魏说:“做文旅急不得,得像博物馆里的文物一样,得经得起时间打磨”。